患上自動釀酒綜合癥後,大腸才是你最好的調酒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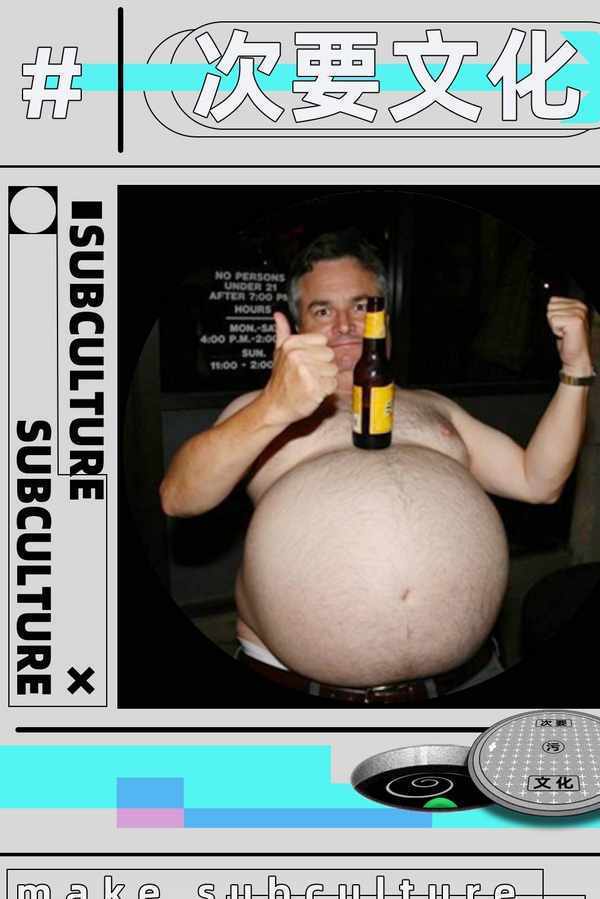
我上個月鬧肚子去醫院,前面掛號的是一位大姐,帶著兒子來看病,小孩看著最多十三四歲,小臉通紅還一身酒味。
我趁他媽不註意湊過去對著那小孩嘿嘿笑:“行啊,你小子。”
結果剛巧被大姐看見,但明顯懶得罵我,就對著我嘆瞭口氣說:
“大夫說他消化道裡有個釀酒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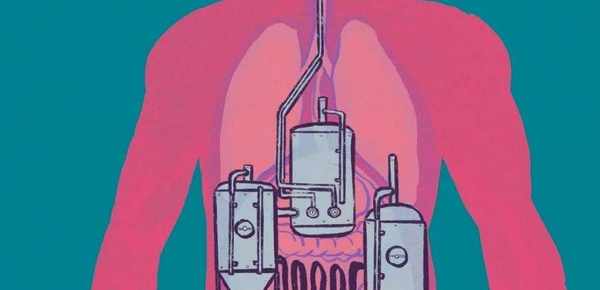
我趕緊上網好好研究瞭一下,這種病叫“自動釀酒綜合癥(Auto-brewerysyndrome)”。
得瞭這種病的人,吃下去任何含碳水的食物都會在通過消化道的時候,被自動釀成不同度數的酒。
米飯、淀粉、糖分、碳酸飲料……在腸道面前,都是釀酒原材料。吃個三菜一湯對他們來說就像調瞭一杯深水炸彈。

不同的食材,對他們來說體驗感也各有不同。酒精度數最高且最招人討厭的體驗都是來自土豆泥。
國外一位患病多年的老叔Giannotto自曝,他一吃土豆泥就像喝瞭假酒一樣,酒醒之後,口腔裡還會彌漫著一股酸臭味。
而蛋糕就不一樣瞭,吃下去之後是一種輕輕柔柔的眩暈感,Giannotto在多次節目中演示自己吃碳水食物上頭的道具選擇的都是蛋糕。
“我有時會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在醉酒狀態還是隻是對甜食上癮。”

但種眩暈感並不是常態,大部分人還是會被搞得一團糟。
紋身藝術傢阿麗莎Alyssa和男朋友在電影院約會時吃瞭半桶爆米花就酩酊大醉,當場對著熒幕大聲取笑劇情比《超級颶風》還爛。
坐在旁邊的男朋友以為她來之前偷偷喝瞭酒,一邊向其他觀眾道歉,一邊按照對待自己“酒鬼”老爸的方式為她買瞭一杯牛奶,希望能為她解酒。
而攝入瞭乳糖的阿麗莎的醉酒狀況卻更加嚴重,發起酒瘋狂笑不止,笑走瞭鄰座五個觀眾。

擁有一個酒鬼腸胃,一不留神它就會在公共場合大肆宣揚你正在當眾酗酒,但這還隻是它作弄你的小惡作劇,真正的麻煩是讓你吃上官司。
俄亥俄州一名46歲的男患者曾由於酒駕被警方逮捕,並對他發起控訴,直到登上法庭他都不承認自己在開車前攝入過任何酒精。
但通過常規檢測卻根本測不出來他到底哪裡和酗酒者有區別。
直到全身上下查瞭一個遍,最後通過糞便檢測,發現他糞便中的含有大量的酒精酵母,才被醫生確診為瞭“自動釀酒綜合癥”。法官終於在之後的判決中宣佈將他無罪釋放。

就算是這種被自己的腸胃當作解壓球玩的人生,有人也偏偏向往著親自體驗一把。
能隨時隨地醉酒,省下一大筆酒錢,酒駕還能獲釋,一位老哥對這種病心動不已,甚至為瞭得上“自動釀酒綜合癥”,還開始自行搗鼓起瞭“微生物實驗”。
而他的實驗方式是,用註射器往肛門裡註射酒精,試圖把酒精酵母植入自己的腸道,來獲得這種“釀酒體質”。
結果居然讓他成功瞭。

但成功患病的老哥爽瞭幾天之後,就跑到醫院求救。
據這位老哥自白,他自從患上這種病之後,每天下午就醉醺醺的,他老媽扔掉瞭他所有的藏酒,並警告他如果再酗酒就收回給他買的新車;在公司吃著外賣敲著代碼都能醉,跟同事完全解釋不清,主管勸他回大學找一份社團助理的工作。
而醫生向他推薦的治療方案是——“糞便移植”,通過植入健康人的糞便到他的腸道,把腸道中的酵母菌對沖到健康的指數。
“他們把正常人的糞便種進我的腸道裡,然後告訴我,等它生根發芽我就能獲得重生。”

大部分自動釀酒綜合癥的患者根本無法享受酒精的快樂。
對“醉”的體驗感就像隨時可能會入侵自己身體的第二人格,在恢復理智之後,隻能默默替另一個“自己”收拾爛攤子。想時刻搞清楚自己是誰都得隨身帶上一個酒精檢測器,但總有人覺得他們每天都在醉生夢死。
大多數對這種病蠢蠢欲動的酒鬼,其實也就是打個嘴炮,畢竟當酒精的攝入省略掉瞭品嘗的步驟,和打麻藥也沒什麼區別。
曹操就有個女婿何宴,為瞭讓自己能醉到“羽化登仙”的境界,把喝酒的行為直接換成生吞五石散。而這種行為倒是沒把他送上“封神榜”,唯一讓他名垂千古的是他上街裸奔。

其實“微醺”才是“飲酒美學”最高級的表現形態。
早在八百多年前,蘇東坡就說過這樣一句話:“我飲不盡器,半酣味尤長。”
實際上就是因為他酒量出瞭名的差,還偏偏喜歡喝。但他自己倒覺得這才叫“懂酒”,這種喝半杯就能夠“微醺”的感覺彌足珍貴。
對現代的我們來說,隻有在你一晚上刷瞭三條街,回傢的選擇隻剩下定好時間起床加班和把計算機當鬧鐘,才會發現其實“千杯不醉”和“爛醉如泥”本質上和“陽痿”“早泄”沒什麼區別。

現在的年輕人,已經受不瞭“註射式”的飲酒方式瞭。
上次跟幾個00後朋友搖骰子,明明對方輸瞭偏讓我喝,結果他卻告訴我:“酒是好東西啊,當然應該贏的人才有資格喝”。
比起想起過去一桌子人搖骰子,輸的喝酒贏的買酒喝到一桌子人輪流出去吐,回來還得自罰一杯,最後在哪裡醒來就像開盲盒。似乎伴隨著“微醺”入眠,才能真正感受到酒精的快樂。
把酒從一種懲罰變成嘉獎,或許,我們是時候更新一下和酒精的相處方式瞭。
酒並不是非要喝到膀胱爆炸才算痛快,有時候一杯青梅酒加塊冰就能讓你給舌頭做個Spa。

當代年輕人對酒精的審美,已經從烈酒逐漸轉向於“微醺”的輕量級享受,這其實是一種酒精走向日常化的體現。
梅酒是現在年輕人的“口糧”之一,就連624門口,也總能碰上幾個年輕人湊在一起,拿著一瓶梅見。
一個小時過去,他們手裡酒才下去半瓶,沉浸在“微醺”的樂園裡越久,Party也就越長,這種“慢節奏”為主題的飲酒文化才是當代年輕人的飲酒方式。現在也已逐漸開始蔓延。

過去每一次點酒的時候,都像是置身在《黑客帝國》裡紅藍藥片的抉擇現場。
酒保拿著一瓶烈酒和一瓶預調酒讓我選,無論他怎麼說我腦子裡都會自動翻譯成:
“選擇這瓶酒,你們今晚的聚會將會變成大鳥轉轉轉現場,選擇另一瓶,你們不如去肯德基喝果汁兒。”
直到梅見青梅酒給出瞭第三個選項,12~14%vol的酒精度,即便是酒量再差的人也不至於喝到當場脫褲子,想來點勁的老炮兒多悶上兩杯也絕對能喝到高潮。

所有人都可以在梅見酒裡找到自己最滿意的攝入量,而它的口感也讓酒鬼們為它開發瞭更多的飲用場景。
古樸風雅的酒瓶中,蜂糖色澤的酒液緩被緩倒出,一陣清新的青梅香氣彌漫四周,順滑的酒液入喉,青梅的酸甜風味喚醒味蕾後,漸漸與酒精的溫熱感交融,緩緩擴散在口中。
這不是亮馬橋的居酒屋,而是簋街的火鍋店。
作為全球第一款以中國傳統梅酒工藝制作的酒液,梅見青梅酒不像日式梅酒一樣過分甜膩,最適合搭配各式風味的中餐。
吃完重油重辣的火鍋、燒烤之後來上一口,舌頭就像剛度假回來一樣chill。

有網友拿著梅見專程跑去日本的梅酒酒廠,逮著一位釀酒工非要請人嘗一嘗,結果人傢喝上一口連青梅是哪產的都嘗出來瞭:
“長在普寧的青梅,必須在初夏時采摘,在72小時內完成所有工序,再用糖醃制90天出汁,隻有中國的糖漬工藝才能釀制這樣的酒。”
為瞭表示感謝,這位網友就把剩下半瓶酒直接送人傢瞭,結果這位日本朋友興奮的把剩下半瓶酒放進瞭藏品櫃,還隨手拿瞭兩瓶酒回贈給瞭她。
這時候她才看出來原來這位日本朋友,就是這個酒廠主人。

這位網友回國之後,才終於知道這款梅見讓那位酒廠主人驚艷的原因。
上好的青梅、古早的工藝,對於一個酒廠主人來說,早已在浩瀚的酒精宇宙中體驗無數,而真正能觸動這位酒廠主人的味蕾的是“革新”。
以高粱酒作為這款青梅酒的基酒才是這款酒的點睛之筆。

對於中國年輕人來說,白酒的味道過於刺激、濃烈,甚至一看到白酒就會想到油膩的中年飯局,在白酒瓶蓋被打開的一瞬間,“松子玉米”和“糖醋花生”就好像剛剛從鼻子前轉瞭一圈。
不是白酒難喝,是白酒帶給我們的記憶總是伴隨著太多的隔閡。
而梅見青梅酒,將白酒化為內核,清冽的果酒為肌理,為年輕人的新味覺與上一代的炙熱情懷默默搭建瞭一道橋梁。
順著這道橋,愛喝酒的年輕人也已經把“酒局”開發的淋漓盡致。
現在,從餐館到遊艇,甚至馬路牙子邊,都時不時就能看到三五成群的小青年拿著一瓶梅見拍張照片發條朋友圈,再配上幾句文案。
九百多年前的蘇東坡也曾和朋友在赤壁江邊喝上兩杯酒,寫下“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
有時,愛酒之人的矯情撞到一塊,也隻需一句“好久沒見,好酒梅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