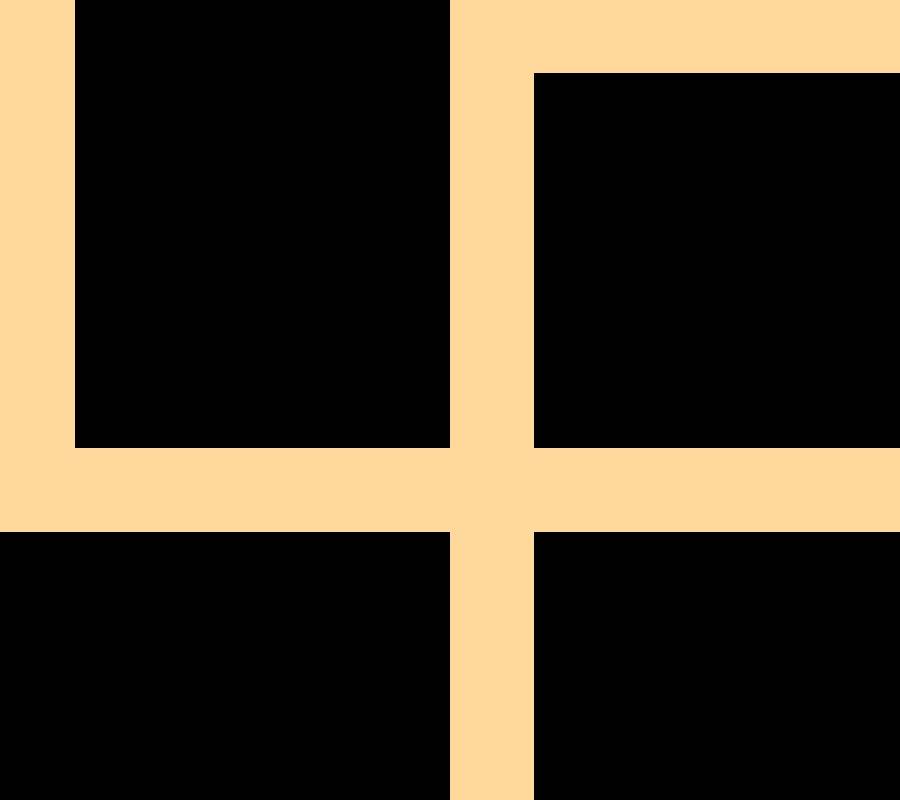君竹:冬日酸菜香
時令到瞭冬季,無論南方北方,傢傢餐桌上都少不瞭一盤酸菜。
作為一種冬季貯藏蔬菜的妙方,酸菜是將新鮮蔬菜經醃制後得以長期保存的特殊菜品,其制作歷史可上溯到周代,《詩經》中記載:“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註釋:“菹菜者,酸菜也”,而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也對“菹菜”(酸菜)的制作流程有詳細描述。雖然後來按照口味風格形成瞭東北酸菜、四川酸菜、貴州酸菜等,但制作方法大體類似。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在生活中不斷實踐,使酸菜不再拘於區域限制,在不同地區形成瞭具有當地特色的醃制方法,如此延續流傳下來,無論富戶貧傢,冬天的酸菜始終是傢庭餐桌上的重頭戲。尤其在生活還不富裕的年代,物資缺,菜品少,到瞭冬季,誰傢如果不醃上幾缸酸菜,恐怕隻有吃白飯,喝西北風瞭。
對於普通傢庭婦女來說,醃酸菜幾乎是一項必備技能。

每年霜降一過,母親便做好醃制酸菜的各項準備瞭。用料不外乎胡蘿卜、白菜、芹菜等,先清洗幹凈,然後或鋪在笸籮裡,或掛在繩上晾曬。那段日子,傢裡的小院像擺起瞭龍門陣,低頭抬眼間,都是各色蔬菜。待蔬菜充分晾幹後,先要用滾水燙一下,然後擠幹水份,再往幾個備好的陶瓷缸裡歸納,鋪一層菜,灑一層鹽和八角、花椒,再鋪一層菜,再灑一層調料。如此這般,幾個菜缸裝得滿滿當當,還要在菜頂壓一塊幹凈的大石頭,才算初戰告捷。等醃漬兩三天後,要加入漿水,一般用煮熟的米湯汁兒,沒過菜即可,最後封口,剩下的就交給時間瞭。大概一月餘,母親往往會醃得更久些,算好啟封的日子,揭開缸蓋,滿屋會散發出一種特殊的香氣,此時即大功告成。
母親的酸菜因為調料放得足,時間掌握恰當,所以特別美味爽口,在酸味之外,還透著一股清香氣息,使這本來寡淡的菜品有瞭豐富醇厚的回味,經常一碟酸菜上桌不久便會吃得精光,要不是母親說酸菜不能多吃,真希望能再來一盤。
除過蘿卜、白菜,母親還找到另一種制酸菜的食材。起初門前的菜圃裡冒出一叢幼苗,傢人並未在意,沒想到這苗子長得極快,且葉片肥大,剛到夏天,已竄到一人多高,在一片低矮的菜苗間很有些鶴立雞群。大傢不知何物,哥哥幾欲拔去,母親急忙阻攔,說這也是一種蔬菜,將來可作酸菜用,大傢將信將疑。等到瞭秋天,折去菜桿,挖出根莖,其形狀與生薑類似,據說這叫“菊芋”,俗稱“洋薑”。母親將其洗凈晾幹,放進酸菜缸裡醃制。傢人很快將這件事情忘記。忽一日,母親端出一盤酸菜,銀白透亮的薄片,晶瑩溫潤,像一片片玉石,食之則脆嫩爽口,酸香繞舌,十分美味。一傢人大喜過望,第二年,那塊地裡又冒出比原來多一倍的洋薑,第三年則更多,這樣,母親幾乎不用再買其他蔬菜,傢裡的兩口大缸都被洋薑填滿瞭。

後來我們隨父親舉傢遷往城市,那塊菜圃也隨之荒廢瞭。然而母親在搬進城市後不久意外遭遇瞭車禍,驟然間離開瞭我們,此後再未吃過母親醃制的酸菜,而洋薑也從生活中銷聲匿跡瞭。
多年之後,在城市的一角又邂逅瞭一款美味酸菜,品嘗之下突然找回瞭失落多年的味蕾。那是一小缸酸黃瓜,放在一輛已經老舊的竹制嬰兒車裡,一位年邁的老婦推著它站在巷口,我確定這些酸菜是老婦手工醃制的,走過去品嘗,立即被那味道俘獲瞭,那種酸味後包含的咸、甜和各種大料的餘香,滋味綿長,簡直和母親醃制的味道一模一樣。以後每次經過,我都會買些帶回去,有時很晚瞭,看她瑟縮在冬日的寒風裡還不肯離去,心中不由生出一絲憐惜。
然而有一天,當我再經過那個巷口時,因舊城改造,巷子裡低矮的老屋已化為一片廢墟,從此再未見過老婦的身影,也再吃不到那可口的酸菜,為此我惆悵瞭很久。
後來生活條件好瞭,有瞭溫室大棚菜,即使冬天也有新鮮蔬菜食用,酸菜逐漸退出餐桌,隻是作為人們的開胃菜、下飯菜。醃菜缸也被束之高閣,超市、菜鋪隨處可以買到成品酸菜,人們再也不用為貯藏蔬菜而煞費苦心瞭。
可是一到冬天,還是非常懷念母親手工制作的美味酸菜,那種愛心的浸潤,情感的醞釀,早已超出食材本身的含義,成為一種深入心魂的精神滋養。